.jpg) 根据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,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。著作权属于作者。按照文义解释,作者有两重限制,第一必须是公民,也就是自然人。之所以出现法人、其他组织被视为作者,是由于法律上的拟制。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,第二个基础是需要“创作的内容构成作品”。我国《著作权法》中规定的“作品”是“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、艺术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工程技术等作品”。
根据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,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。著作权属于作者。按照文义解释,作者有两重限制,第一必须是公民,也就是自然人。之所以出现法人、其他组织被视为作者,是由于法律上的拟制。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,第二个基础是需要“创作的内容构成作品”。我国《著作权法》中规定的“作品”是“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、艺术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工程技术等作品”。
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则进一步规定“著作权法所称创作,是指直接产生文学、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”。
由此可见,根据著作权法的逻辑体系,作品、作者、创作行为和著作权利益的分配是密切相关、环环相扣的。抛开后续的利益分配,至少在作品、作者、创作层面,有作品才能判断作者,才能称之为作者,而只有作者才能创作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,作者生产作品的过程才能称之为创作。
基于目前我国的《著作权法》立法内容可知,著作权法中第一位的作者必须是具有创作能力,已经通过智力活动产生了在文学、艺术、科学领域内生产出作品的自然人。因为公民方能成为作者,而显然我国还没有开始赋予任何动物或者人工智能公民法律地位,哪怕是类似法人的拟制地位,由此,按照文义解释,即使人工智能在将来生成的内容具有相当程度的“独创性”,只要著作权法关于主体的规定在立法层面未发生变化,人工智能将很难成为作者。
我们回顾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》似乎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。公约保护的作品范围是缔约国国民的、或在缔约国内首次发表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。而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,联盟任何一成员国公民作者,或者在任何一成员国首次发表其作品的作者,其作品在其他成员国应受到保护,此种保护应与各国给予本国国民的作品的保护相同。因此,公约旨在赋予自然人(法人)作者平等享受著作权保护的权利,而并不可能涉及对“人工智能”的赋权。
回望历史,从“创作”的角度来看,亦有学者深刻的指出,“创造” 概念的历史性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,它以意志自由为中介,构成近代哲学中的人性基础。美学和法学都把作品界定为“表达”,这个词已经暗示了主体的能动性。没有驱动表达的自由意志,至少在哲学意义上,生成符号形式的行为不是创造。”
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中,裁判者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“若在现行法律的权利保护体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、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,则不宜对民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。故本院认定,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……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,因此,即使某法律数据库‘创作’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,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,依然不能认定某法律数据库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。”
但是如果不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界定为作品,不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一行为定性为“创作”,是否会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?目前的判断是否过于缺乏科技发展的眼光呢?
笔者以为,现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,即使是更接近于人工智能本质的写诗机器人,“除了存有创造力、情感等方面的‘AI通病’之外,逻辑不清和语义不连贯也是其所存在的突出问题。”[3]除了生成内容有无价值是否值得保护之外,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能够商业变现也仍旧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即使有朝一日,人工智能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利益,其实也无需过分担心。“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符号表达在财产价值上与作品相当,也需要法律分配利益,这倒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。创造原本就是权属依据之一种,引入其他因素作为分配依据并没有什么障碍,现行法已经把资本、效率等其他因素也作为权属分配依据。”[4]
现行著作权法将投资者、法人、其他组织等拟制为作者或者著作权人,已经表明,即使不是作者,也能够成为著作权利益分配的受益者。“知识产权法基本功能的表述可以修正为:分配基于符号表达所形成的市场利益。”[5]正如一些学者所说,人工智能创作内容利益的实现,至少在目前阶段,似乎并非必须改变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概念或者创作概念以削足适履,法的安定性考虑似乎更加重要。只要能够在满足法律解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,妥善处理利益的分配问题,一个机器人是不是作者、其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作品,反而没那么重要了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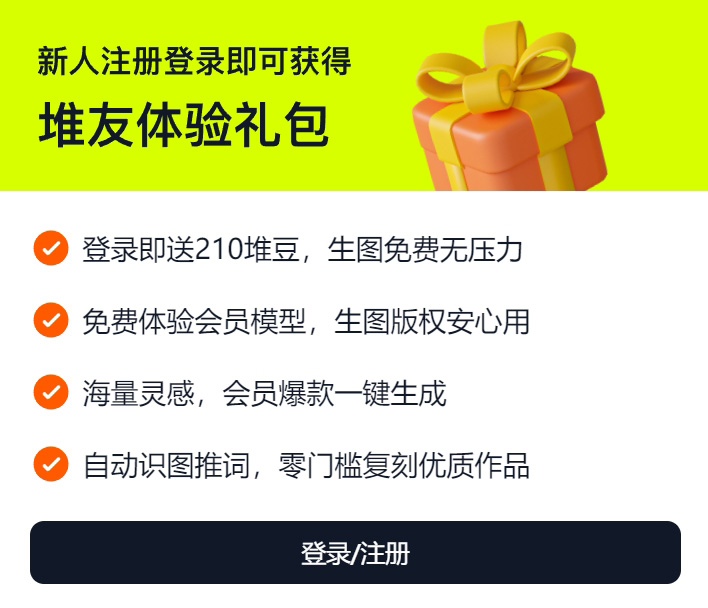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津公网安备12011002023007号
津公网安备12011002023007号